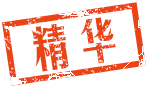请马上登录,朋友们都在花潮里等着你哦:)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账号?立即注册
x
本帖最后由 书洛 于 2017-12-22 11:49 编辑
花木兰
女子谁人爱沙场。可是,为了血脉亲情,那一腔滚烫必定单纯而汹涌,于是,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
我问友:你说花木兰是不是一身好武艺,不然怎么战场上闯荡十二年,还能存活得挺好?玩电脑的友乜斜我一眼:嗯,应该有武功底子。这什么结论,整个儿把一个当户织的小女子生生说成了江湖惯犯。
有时想想,十二年的沙场之上,可能真有个文泰,或者张泰李泰什么泰的。否则,世间名利,我想都没想过,江山与我,啥关系呀。心中无所搏求,沙场之上,如何有力气撑起一条原本娇弱的生命,何况,一撑就是十二年。当是有爱的,有那个爱她也让她爱的人,可以不言不语,却一个眼神就可以搭到,一场厮杀下来,并肩血染战袍。
沙场之上,如何言爱,今天你用水刷的是离去战友的腰牌,也许明天,他便刷着你的,或你刷着他的。可是,当我们能够言爱时,就怕,爱已不容我们出口。哪怕我们都能够出口:放弃生命容易,放弃你,太难。可是,爱,却已不能够,它只能拍拍我们的肩,然后送我们反方向的各自出走。
那个用最豆蔻加韶华惊艳了尘埃万千惊艳了见血见骨的沙场的女子啊,我多希望,当她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时,撩开帘栊推开门轩,她与那人能够目光明亮如银的彼此烁烁相耀,不带一丝阴霾泅潜。
可是,若结局是这般:他说,忘了我吧。她说,因为你在,我才有勇气把眼睛睁开,以后每一天,也都会这样。也不能解读为爱如衣破,尘埃前裂帛。
或许,我们的爱里呀,总会有细作,手段一般的,或许还能降服,手段了得的,我们便只能静观其变,动心却要忍性,动到会疼,忍到始终。
爱若问我:你不怕失去会疼?我笑,哪里不会疼,走路碰到会疼,身体不适会疼,得不到会疼,放不下会疼。可是,我必须行走,逢遇则爱,逢散不哀,这是天性。
爱,是因为,他是你的良人,疼,是因为,他是你的冤家。无论是埋首金沙堆还是陷落粉花垛,那一颗心呐,偏偏就横在了他的手里。干嘛呢?给他绣上我的名号。
三请樊梨花
梨花两个字,配上岁月,配上山川,就是配上雨凉都好听,唯独配上薛丁山,最不招人儿听。
他说:我很色。我说,很正常,男人当如是。其实,不独男人,还有一句俗语:姐儿爱俏。樊梨花唱了10个爱老薛还没唱完,接着再往下爱的时候,被时光打了岔。统计来统计去的,也不过就是爱他长得好,从头顶的盔到身穿的锁子甲,从白马白枪到打将钢鞭,从胸前元帅印到执掌的兵权,这位大姐呀,这哪是他长得好哇,这分明是人家外表精装修,好不好?
长得好有啥用,这个老薛相当的不厚道。人家为他弃亲人投唐也不对,舍前嫌救他命也不对,收个养子也招来不贞的是非。这位大哥,你是有多牛哄哄?不过就是一个位为人臣的官二代,还真当自己是震主的天神啦?
梨花同学这数上10项都数不完的爱,换来了啥?二更里梨花听风吹竹帘冷,三更里梨花上床独眠凄凄,四更里梨花开始做梦,五更里正梦到与他团聚。忽然一声鸡报晓,为这声,还把小金鸡骂了几句,怎么起得这么早,把我的好梦给冲没了。这份爱里,她到底上了多少次为他的妆,却,每每哭花了再重上。
我曾看过一幅樊梨花的画像,金甲衣裙,桃花马旁手执绣戎刀。想都可以想到那时她瞳色清透,她如补天俏云,如一场桃花汛,扑湮了历史的堤岸。何苦,何苦就被挡在了那个叫薛丁山的矮树墙头。
有人说,现今,是个缺乏传奇的年代。而那时,樊梨花就如沙场为将一样,毫不犹豫而身份分明的,就把爱之阕如拓成了烈焰扶盟。她要新桃团团,她要阅色复香,她要旧眉不薄,她要常和羞走。
她为一眼认定的良人而谦卑,十分本领九分敛,枪到胸前又收回,就连把那么个大男人挑下马来都惦记着要轻轻。可是,做女人终究不能太轻贱了自己,当亲人血涂染的寒江关拱手奉上,当不用花轿来抬自己主动跑来以身相许,她大抵就失去了让他用心尊重的筹码。于是,那良人,披上了冤家的面皮。
所谓传奇,就是这般吧。爱,不问该不该,不问值不值,不求对等甚至不问公允否。爱,就是心中一朵莲花,不论良人凌波,不论冤家浑浊。
穆桂英挂帅
多年后,杨门十二寡,像一幅九九消寒图,而为她们涂上鲜色的,是穆桂英。
五十三岁,头戴金冠压双鬓,一身铁衣鳞,一杆帅字旗,一个头大的穆字,那时人呼她为“浑天侯”。辕门外三声炮响,是催她走上沙场的号角,她有不甘,她有不愿,但回过头,看一看自家的老爷,华发如霜眸已不再清澈,却依然以崇敬的目光看她,于是,她心安了,她甘愿了,纵使国已腐朽,他若赤子,她便决不允许别人轻薄了那颗丹心。
犹记那年,他白袍白马杨家枪,主要还是翩翩少年郎。要不怎么说,姐儿爱俏呢,世间道理总是归置的如此妥当。大战她一百二十回合,却被她挑下马来。这情景有点像樊梨花,可是,桂英到底比梨花馥郁秋盛,她的宗保不是薛丁山,她的宗保阵前娶她,又与她举案齐眉心相悦,却被公公降了罪。而她如何是那般认了命低眉认输的人?公公你技不如人,这可不怪我,闯帅帐救我夫理所应当。
凭本事的女人,终归谁也看不低了去。看她挂帅直破辽军七十二阵,桃花马上挥兵风雷动,沙场上敌血飞溅石榴裙。呔,叫一声番王你听真,我一剑能挡你百万的兵,你信是不信,服是不服。她是如此嚣张又如此耀眼,如此铿锵又如此绝艳,忽然想起看过的一句话,便是送给那倒在她剑下的人:最后看她一眼,死亡之路上竟也走得春心荡漾。
从此,她是宗保的妻,而宗保是她的命,她为守护他而来,为成全他而来。其实在杨门女将的版图上,她算是最完整的一块儿了,有夫有子,上有护下有爱。五十三岁出征,还能有那个从少年时叫相公,到此时已被称为老爷的人,与她并辔而行,那因缘,到底是给了她从头到尾不留白的媚好。她当去爱,却不要爱得江山成苍,黎民阑珊。
好啊,那就这样吧,她早早接受了的,即使为了他--这个她在洞房花烛时曾纤指点额小声薄嗔过的冤家,必是要生在沙场,爱在沙场,甚至同死沙场。可是,她还是认为,这人世,多好,国在,家在,良人在,冤家在。
这般因缘,世间总有一处。他说,我爱你,只爱你,你不知道?她说,知道。所以,冤家时,含泪睡去,良人时,微笑苏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