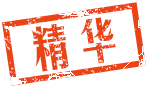请马上登录,朋友们都在花潮里等着你哦:)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账号?立即注册
x
本帖最后由 西风烈 于 2024-10-27 22:51 编辑
酒店大厅的大立钟敲响晚8点,我的安全巡查也就要付诸行动了。其实,酒店的消防安全是相当到位的,几乎不可能存在隐患。我主要看看客人有什么需要,以便尽快落实他提出的一些想法。616号房间入住了一个部门领导,是首先要去巡视的地方。我整了整红领结,预备进入这套房间做初步安全巡视。 我挺了挺比较板正的身姿,伸手按响了房间门铃。我之所以要特别地挺挺身子,是为了维护酒店形象的做法。门铃声响过一遍,房门被悄然无声地拉开了,一个穿休闲装的男人站在了门口。他的相貌看去隐约有点熟悉,但我没往深处寻思,不动声色地瞄了他一眼后,我不觉有些迟疑地站住了房间门口。
是你吗?老同学在这里上班啊?男人问话的语气很惊讶,也很激动。看得出他的表情是真挚的,不是装模作样的,形体动作也透出一股亲近感。 可我还是按捺了怦然的心跳,摸不清他是在试探,还是随意发挥的问。人家毕竟是区级领导,身份摆在那里,我一介小保安得检点,不要轻举妄动。 再说规章制度指明,酒店人员是不能随意与客人聊天的。每当客人下榻酒店,我只能按照工作要求,在客房的茶几上,放下一个彩色推广宣传小册子。
男人的亲近感禁不住让人轻易拒绝,我突然失去了自己情绪的控制,一句顺其自然的问话,从我的口腔里迸发了出来:“你是陈局长吧?”我也突然惊奇自己的声音,激动与惊讶中带着一股家乡的口音。“听说这套房间住着区公安局的局长,搞了老半天没想到是你啊!”吐出来的家乡口音是越加重了。
老同学啊,咋地你也搞这一套?还是叫我的姓名吧,别局长局长的叫了,太生分了不是?现在一时半会没别的啥子事,进来随便坐会嘛,也不会影响你的工作。哎呀,这么多年一晃就溜走了,想着哪天遇着了咱们就多说说话!
我一直像一只渺小的蚂蚁,靠老乡关系进了“丽景大酒店”,默默无闻地做着保安工作。“丽景大酒店”是家标准三星酒店,可对于我来说只要当好保安就够了。如果今夜不是他来“丽景大酒店”做安保,也许我这一辈子都不会遇见这位政务人物。20年后的一次偶然机遇中才知道,我俩就生活在同一座三线城市,尽管做着类同的事,却是20年来哪怕是一次巧遇都没有发生。 这天突然得到老乡经理通知,省纪委巡视组来小城检查工作,就选在我所在的“丽景大酒店”下榻入住,他告诫我们服务人员说,一定要借此良机把酒店的招牌名声扩大到省会去。我跟所有勤谨的服务人员一样,理所当然地尽职尽责做好本职。市公安局自然也得到了消息,他们闻风而动雷厉风行,当即指派区公安局迅速派员出动,奔赴纪委官员下榻的酒店,认真完成安保服务。 老同学再次对我招招手,饱含了期待的目光,示意我坐在他的旁边。老同学原名叫陈祖佑,后来看了《陈真》的电视剧,他就自己改了名叫陈归真。 好了,我就就按老同学的叫法,叫你小右派吧。毕业后突然断了你的消息,快过去20年了,说说你丰富的人生经验,让我好好领会学习一下吧。 我依然站在了陈归真所在的沙发旁,尽量压抑着内心那份尴尬的心情。
分开20年来时光,如珍宝般的时刻,日积月累的淡忘不就生分了。相互所处的境遇不同,生分如同横在我们之间的沟壑,谁都不想轻易跨越。青涩岁月里的故事,早已失去原本烂漫纯真的味道,却又无法在记忆里随意抹掉。 真可谓一言难尽啊!陈归真从茶几上拿起一支“牡丹”烟盒,揭开盒盖子,抽出两只香烟来,朝我的面前递过来一只。我摇晃着双手推辞了后,他的脸色很淡然并没显出尴尬,照常拨燃打火机点燃了被我推辞了的那只香烟。
当初并不是我有意不告而别,我也是迫于无奈的。我是想让自己混出个人样再回归而来,走的时候除了我的爸妈没告诉任何人,你不会怪我吧?” 事情都过去了20年,就让它随风而去吧。 你对内中的原因是不愿意听听吗? 这是说哪里的话,如果你方便,你说给我听自然乐于听命。 陈归真仰在椅子背上吐了几个烟圈后,带着不急不缓的语调诉说起来。
你是知道的,我爸在“永红”机械厂做会计。年末的时候,老爸下班回到家里,脸色显得很难看。我妈招呼他擦脸吃饭,他低头沉默了一会对我妈说,他做了一件很大的事,或许有很不好的结果,希望我妈这辈子不要怨恨他。他这样麻起胆子做,也是出于现实无奈,也有他一番苦衷,下不为例地做了。
当时我们正在读高中嘛,学习紧张得够呛,我妈自然不会告诉我这些的。直到毕业考试完回家,我看到我妈躲在角落里哭。我再看我爸没去上班,羞愧难言的样子劝慰我妈。家里出了遭天的事,我爸知道瞒不下了,两手搭着我的肩头,把我按着坐在了吃饭的凳子上,两眼泛红对我说了事情的前前后后。
厂长挪用了厂里大量资金,要我爸帮他在账面做手脚,把账目抹平。厂长答应事后会给我爸好处。你知道我妈没工作,她是常年有病在身。我爸的工资除去给我妈看病吃药,剩不了多少,家里日子很艰难。你想想看,如果帮了厂长的忙,我妈就可去大医院看病,自然好得快,家里的生活就会改善不少。
我爸说他当时并没马上答应,做假账虽不容易可还不是难事,他只是以沉默不语地抽烟来拖延回答。我爸他说他深入地考虑了一番,迫不得已勉为其难地答应下来。后来果然东窗事发,那厂长被就地免职了,退赔了大部分挪用的钱,扣发了一年的工资,不知怎么调到其他单位,并没因此受到更大处罚。
而我爸低估了这事的影响作用,以为最多挨个处分差不多了。不知道还牵扯到其它领导,没多久就被厂里背后除名了,并没有公开的正当理由,说是要留条后路给他。我爸这下整得失业了,也没其他单位接受,家里没了经济来源。我爸只好一边打零工一边到部门上访,家里都揭不开锅了,他坚持上访讨要说法。我妈受到打击病得更厉害了,得不到起码的看病就医,情况越来越糟。
好在校长看在我爸是同学的情面上,替我的家庭情况保了密,又推荐我当了坦克兵,希望我在部队混成人样,不再让爸妈往后在人前抬不起头……” 陈归真嘴边的那只香烟剩下了烟蒂,被他抽出来轻轻摁在烟灰缸里,随着吐出来的烟雾的逐渐消散无形,一段难以言表的生存经历也随之诉说完了。 也说说你过来的生活吧,这么多年想必你也会遭受到不测。陈归真说着从床头一侧拿起了提包,随意地一把拉开,从里面掏出一小包茶叶,起身走到饮水机那里接了水,来到沙发茶几的跟前,倒了杯热茶放在了我的面前。
唔,我的生活如同这杯茶水,平淡无奇得很,没有一点波浪起伏。捧着有些发烫的杯子,我索性坐在旁边短沙发上,开始了简略性的一段讲述。 那年高考败北后,我无心参加复读。我爸只好提前退休,我顶了他的职进了“劲松”纺织厂上班。上班轮流倒十分辛苦,每月能拿到工资倒也知足。直到两年前,工厂以扩大规模为借口,转卖给了私人老板。谁知那老板接手后却关闭了工厂,直接拆除了厂房,盖起了商品住宅楼。有人接连告到市政府后,厂里只补发3万元安置补偿,就让我们各自开展创业,说是实行改革开放。 那年我才22岁嘛,找个地方吃口饭也不算太难。正好我遇见了一个老乡,就来到这家酒店上班。可是,工厂当时还欠我们半年工资没给,那可是日夜上班劳作的血汗钱。为了这件事,我们几次到市政府上访请愿都没有结果。
也去上访?我劝你们放弃,不做无用功吧。我爸上访那么多年,把家里的日子过的不成样子,也没捞个好的结果。到老了,只能靠我来养活他们。 以前去搞是行不通,现在是省委巡视组到家门口了,应该可以找他们上访啊。我突然冒出这句大胆推测的话,且说这句话的语气有些理直气壮。
你还是初出茅庐时的样子,单纯率真得可爱。事情哪有你想的那么简单,省委巡视组是带任务来的。不过嘛,真要这样有位硬手倒是可以帮到你。” 这是哪个?真有一把刷子?我大为吃惊,觉得这样的人不可思议。 隔壁巡察组的组员魏源,他原本是我们区的所长。他这人性格刚强,得罪过不少官员,甚至受到黑道人物的威胁,可他天生硬骨头依然扛得住。
听到魏源这个留存在记忆深处的名字,我心头的震撼不亚于生吞了活蛇。说来魏源所长他和我曾经有过一面之缘,那还是我入职这酒店不久的日子。当时的情势紧迫逼人的场景,到现在回忆起来还让我心有余悸。 那天夜晚,我像往常一样在酒店巡查。可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总感到哪里不对头,有些发慌,仿佛这晚会有事情发生,谁知我的第六感觉撞上了。
在酒店值夜班早已习以为常,熬到了午夜,正准备洗洗休息,值班室的门忽然被人撞开了。我猛地一惊,蹭地坐起了身,惊恐地看向门口。一个陌生男人闯了进来,反过了身把门锁上,再转过身靠在后门上喘了几口气。他忽而跨出几步,冲向床铺边,端起一只床头柜,放在门后面,使劲抵紧了房门板。
做完这一连串动作,他走到我的对面瞧着我,眼神直愣愣的。我俩的距离不过两三米,我分明瞧见,他脖子上往下滴着血,衬衣上淋漓沾染了不少。
男人盯着我瞧了几分钟,见我纹丝不动,便一步走到我旁边的茶几旁,拿起我忘记喝的一杯水“咚咚”喝了个干净,啪嗒一下瘫坐在了我的椅子上。 男人有一张硬汉勃发的脸,可此刻已经消散了血色。他掏出手帕去捂脖子上的伤口,血液汩汩地顺着指缝间渗了出来,然后一滴一滴滴落在地板上。
用毛巾绑扎一下吧。我挪开了脚步有点撑不住气说。 不用。你就待在那里。 他把身体整个地摊在了茶几桌上,像一个醉了酒的汉子一样,找到一个支撑点就将就趴下疲乏不堪的身体。这样不忍直视的情景,让我显得很不安。 我去楼下给你拿点心来吧。我嘟哝着嘴皮吐出了这句话,用手按着心窝区稍微镇定了一会,但内心深处想尽快走出这套房间。 不要出去。不要出去。 他的声音虚弱得像针落在了地上,但我内心感觉有一股礁石般的力阻扰。我的两条腿有点僵硬了,刚刚想怎么挪动一下,却被他说话的威力震慑了回去。轻轻瞥一眼桌上的电话机,就搁在那里,我只要愿意伸手完全能够得到它。
我给你打120,你在流血了`,真有点邪乎。 别打了,躺一下就没事的,你帮我扶起来吧。 我努力把他架到值班室的床上,他闭合着眼,身体软绵绵地躺了下去。 他不会就这样拖延死去吧?再这样耽搁下去怎么行?我连忙转身疾步走向门口去拉开房门,却被门把手上的一缕鲜红的血迹吓得收回了手。 突然,像暴风雨前奏响了一阵闷雷,通道上传来了嘈杂的脚步声。 嘿,看这里漏的血迹,这家伙一定藏哪个房间,他现在跑不掉了! 我触电似地缩回了手,重新把茶几顶在了门后。我不清楚发生了啥糟糕的事,但绝对和屋里这男人有关系。客房外就一条通道,我能跑到哪儿去呢?我就算现在跑出去,屋里这男人一定危在旦夕!让客人无端死在客房,势必损害酒店的声誉!我急忙掏出手机,哆嗦间按错了键,才把报警电话拨了出去。
里面有人吗?里面有人吗?赶紧打开房门,我们要找个逃债的! 我的双腿一阵阵发软,像捞不起来的面条,悬挂在无形的空中,悬在那儿怎么也挪动不了。躺床上的那个男人闭着眼,和死去的模样没啥子差别。看来是昏迷过去了,时间一长就可能随时告别人世。外面敲门的声音越来越紧,似乎不愿意轻易放弃进来的打算,但也像在酝酿着诡计不想轻易贸然闯进来。
可这样的情状到底能撑得多久呢?再拖延下去难道是好的选择吗?再说我稀里糊涂打了报警电话,会不会遭到他们那帮人歇斯底里的报复?我慌乱的心情像插在城头墙上的旗子,来回反复摇摆不定,找不准方向而摆正位置。
你们在这瞎闹什么?不知道这是高级酒店、不是打架场子吗?忽而传来一声威严的怒喝,门口逐渐安静了片刻。随着怒喝声大步趟出一个精壮的汉子,身上的藏黑色警服,妥帖地罩着他的身板,身后紧随着一群昂扬的青年。
魏大所长,是您老啊,这么晚了还在忙哈!我们哥几个邀约喝酒,喝高了来劲儿练练手,您看我们自己解决掉算了,就不麻烦您老亲自上台了。 说话的是开发商老板的儿子,这座城里有名的小爷,没人敢轻易冒犯。
人都被打得那么严重了,你们怎么能够自行解决?还知不知道有法律?赶快把受伤的人送人民医院,其他人带所里录口供,谁都不想轻易逃脱! 我完全被吓懵了,半夜三更经历这样的事,好像一场噩梦。这座城里居然有人不买小爷面子,这样的人少见。我没料到眼前精壮汉子的底气挺大。后来老乡经理背后告诉我,那晚躲在值班室的人上访举报拖欠工程款,遭到那所谓的小爷带领的街痞混混追杀。而当夜处置危急事务的领头人,是区级派出所长魏源。 陈归真先前说过的话让我反复琢磨了好久,心里纠结着利弊关系举棋不定。或许不能因为我牵头出面,影响到巡察组工作,心头翻腾着他说过的那句话: 往后生活上有困难就和我说,我能帮到你就一定帮你。上访的事你不要抛头露面了,毕竟是我带队负责安保工作,你不好让我这老同学为难吧? 听老乡经理说,巡视组明天就要回省城了。这个消息让我忐忑不安。要不要上访讨回大伙的血汗钱,我必须在今晚做出决定。厂里的职工听到了传闻,晚上跑来不少人找到我,群情激奋要讨说法,我毫不犹豫答应一起去上访。
平安夜的那天,正是晚餐时间,但这天已经歇业了。18个中年女人突然闯进酒店大堂,负责安保的公安警察,见情势不妙,没得到领导发出指示,自以为高明地从各处围过来伸出手臂阻挡起来。双方难免地发生了互相推搡,女人们一边奋力往前冲着,一面尖声呼喊到,我们要见省领导!我们要见省领导!
巡察组都住在二楼,电梯门已经关闭,想来她们是无法冲上二楼了。我站在步行通道旁看着,急得浑身骨头发紧,可是没有法子鼓动她们。我朝大堂里搜寻陈归真的身影,希望他能出面告诫公安警察,可就是看不到他的身影。
女人们像找到了某种方式,开始分头往楼上冲。捶门声,叫嚷声,跑步声,大堂里出现了混乱。酒店门外不知咋地挤起了瞧热闹的人,场面有些失控。我只好故意装作劝阻的样子,高声叫喊到,女同志啊,一定注意安全啊!
突然,电梯门豁然敞开了。从这出入口趟出两个人,面色严峻。其中一个身着灰色休闲服,像一座铁塔站在大堂的中央,他的身旁俨然就是陈归真。 都给我站好了,大家别乱套,那样反而会坏事的!有啥问题就和我说,你们这样解决不了事情! 女人们七嘴八舌嚷道,你是哪个?我们的事你管不了,我们要见省领导! 我是巡察组组员魏源,你们选几位代表,我带你们面见主要领导。 人群顿时安静了不少,女人们低声商量讨论一会儿,选出了4个代表,我几乎没有犹豫一点,从步行楼道大步走出来,加入到她们谈话的队伍。
巡察组组员魏源带着我们进入电梯上了二楼,敲响了巡视组领导的房门……
|